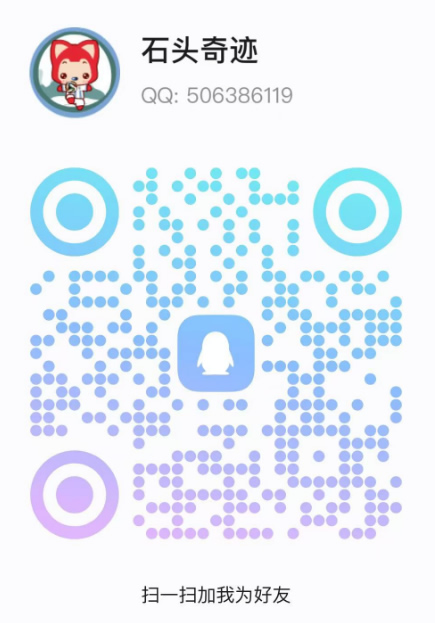奇迹mu黄金文章哪里出,奇迹黄金文章怎么获得
一、奇迹私服里,卓越圣魂凯和卓越毒蛇盾,在什么地方打
普通“毒蛇盾”是45级怪物掉落,卓越的就是45+28=73级怪物掉落。比“毒蛇盾”高一级的盾是“布朗司”掉落等级为54级卓越掉落就是54+28=82级。
所以卓越毒蛇盾掉过的怪物为73~81级因为82就掉落卓越“布朗司”了。
73~81级的怪物有海底的“海魔希特拉”74级、天空的“阿卡摩斯”75级、沙漠的“巨齿兽”76级(铁脊怪72级)、天空的“恶灵”78级、沙漠的“铁轮战士”80级(破坏骑士82级)。特殊地图里的怪有,幻影寺院3的“幻影教亡灵”81级、赤色要塞5-6的怪物70~80级、血色城堡3~6都可以出,3城堡打“骷灵骑士”和“骷灵巫师”,4城堡打“骷灵战士”“骷灵兽”5城堡打“假面弓手”“骷灵战士”6城堡打“假面武士”“假面弓手”。打以上这些怪都会出的卓越毒蛇盾的。
下面是圣魂凯掉落等级为78级(普通的),卓越圣魂凯就是78+28=106级,比圣魂凯高一级的是亚特兰蒂斯之铠掉落级数是80级,卓越级数就是80+28=108级,所以要打卓越圣魂凯就要打106-108的怪、范围比较小所以好找。一般都是刷坎特鲁遗址出废墟的那个区域,打屠杀者掉落、卡利玛6的武士掉落,天魔应该也掉。
好了只要是按照官方设定的,私服制作者不乱改就是这样子了,祝您游戏愉快。
二、谁帮我找一下一篇文章叫《遍地黄金》
遍地黄金
①人蜷缩在湿漉漉的雨季,整个儿像一颗受潮的糖,沮丧而又无奈。
②前日忽然放晴,心,也就跟着晴了。从南窗望去,那边楼缝的坡地上一如往年,绽出一抹黄色。还刚刚惊蛰呢,油菜花这么快就开了?中午儿子放学回家,进门就说,路边的菜花约好了似的,一夜工夫全黄了!下午乘车去市郊,果见满畈满坡一片片明艳的黄,一种生命的喜悦油然灌注全身。
③几乎已成条件反射,人一见到油菜花,忧郁的心境就豁亮了。油菜花,我从小年年见,但着意关注它,是在病重以后。四年前腿骨发生病变,每周需去武汉两次,接受希望渺茫的康复治疗。也是雨季,天色像心境一样阴晦,人默坐车上,打不起丁点精神,对人生已失去信心,甚至对生命也没有更多的留恋。就是这个时候,对车窗外成片成片的油菜花,我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感觉,那种蓬蓬勃勃的美,使我的心情变得轻松许多。它那浓郁的生气无形中感染了我,唤醒了我生命中沉睡的信念,生活是美的,生命是可留恋的呀!从此,每年油菜花开时节,虽是行走艰难,也要拄着拐杖到郊外看看,我才不怕得什么花粉症呢。
④要论好看,任何一种单朵的花都会比单朵的油菜花好看得多,单朵的油菜花细小单调而不起眼,它之所以让我有了生命的感动,是因为这些花是以集团军的面貌出现的,显现出一种浩浩荡荡的生机,一种攻城略地的气势,一种汪洋恣肆的活力。油菜花才真正是太阳之光,是光和热的象征。
⑤多少个响晴天,我恋恋地望着窗外,对妻子说,陪我去看看那些油菜花吧。去了,在地头一站就是好半天。所有的油菜花,不论高的矮的,壮的瘦的,一例顽强地展示着自己那一份生命的本色。它们的黄,既不是初春的柳芽那种嫩黄,也不是菊花、葵花的那种老黄,那是一种青春的黄,黄得明净,黄得酣畅,黄得秀朴,黄得平净如水,黄得恬柔如笑。我偷偷给它取了个名字:女儿黄!灿烂的黄花下面,是绿得发暗的秆和叶,青葱的生命高擎着纯情的黄,托展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的美丽扉页。黄花满眼,清芳扑鼻,看花人沉醉了,恍觉自己也变成了一株充满青春活力的植物。
⑥油菜花似乎不怕雨打风吹,它前谢后继地开着,整体花期比一般的花都长些。菜花开了,再阴晦的日子也不难耐了,那爽心的亮色风雨收不去,望一眼,心田就会洒满阳光,它们其实就是活的香的阳光!更多的时候,我于户内凝望菜花,在病榻上斜靠着,看书倦了,总喜欢透过窗子看对面楼缝里的那片油菜花,那差不多成了一种生命的需要。油菜花谢了,没有画家会为我在窗外画一片女儿黄,但我不会再阴郁,花事一过,就是青阳朗朗的夏季了,阳光里流淌着无尽的菜花黄。我本质上仍是个农夫,春天于我,是希望的季节,更是收获的季节,我收获遍地黄金,那是一年乃至一生受用不尽的黄金!
(选自2004年3月长江文艺出版社《中国精短美文100篇》,有删改)
三、桥跨黄金城的桥跨黄金城——文章
原文如下
桥跨黄金城
作者:余光中
——记布拉格
1长桥古堡
一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。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,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。刮面是水寒的河风,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。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,不但暖目,更加温心,正好为夜行人御寒。水声潺潺盈耳,桥下,想必是魔涛河了。三十多年前,独客美国,常在冬天下午听斯麦塔纳的《魔涛河》,和德伏乍克的《新世界交响曲》,绝未想到,有一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,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。靠在厚实的石栏上,可以俯见桥墩旁的木架上,一排排都是栖定的白鸥,虽然夜深风寒,却不见瑟缩之态。远处的河面倒漾着岸上的灯光,一律是安慰的熟铜烂金,温柔之中带着神秘,像什么童话的插图。
候,在中欧这内陆国家,昼夜的温差颇大。在呢大衣里面,我只穿了一套厚西装,却无毛衣。此刻,桥上的气温该只有摄氏六七度上下吧。当然不是无知,竟然穿得这么单薄就来桥上,而是因为刚去对岸山上的布拉格堡,参加国际笔会的欢迎酒会,恐怕户内太暧,不敢穿得太多。
刚才的桥尾堡矮了下去。在它的后面,不,上面,越过西岸所有的屋顶、塔顶、树顶,堂堂崛起布拉格堡嵯峨的幻象,那君临全城不可一世的气势、气派、气概,并不全在巍然而高,更在其千窗排比、横行不断、一气呵成的逦然而长。不知有几万烛光的脚灯反照宫墙,只觉连延的白壁上笼着一层虚幻的蛋壳膏,显得分外晶莹惑眼,就这么展开了几近一公里的长梦。奇迹之上更奇迹,堡中的广场上更升起圣维徒斯大教堂,一簇峻塔修芒毕厉,凌乎这一切壮丽之上,刺进波希米亚高寒的夜空。
那一簇高高低低的塔楼,头角峥嵘,轮廓矍铄,把圣徒信徒的祷告举向天际,是布拉格所有眼睛仰望的焦点。那下面埋的是查理四世,藏的,是六百年前波希米亚君王的皇冠和权杖。所谓布拉格堡(Prazskyhrad)并非一座单纯的城堡,而是一组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建筑,盘盘囷囷,历六世纪而告完成,其中至少有六座宫殿、四座塔楼、五座教堂,还有一座画廊。
刚才的酒会就在堡的西北端,一间豪华的西班牙厅(Spanish Hall)举行。惯于天花板低压头顶的现代人,在高如三楼的空厅上俯仰睥睨,真是“敞快”。复瓣密蕊的大吊灯已经灿人眉睫,再经四面的壁镜交相反映,更形富丽堂皇。原定十一点才散,但过了九点,微醺的我们已经不耐这样的摩肩接踵,胡乱掠食,便提前出走。一踏进宽如广场的第二庭院,夜色逼人之中觉得还有样东西在压迫夜色,令人不安。原来是有两尊巨灵在宫楼的背后,正眈眈俯窥着我们。惊疑之下,六人穿过幽暗的走廊,来到第三庭院。尚未定下神来,逼人颧额的双塔早蔽天塞地挡在前面,不,上面;绝壁拔升的气势,所有的线条所有的锐角都飞后向上,把我们的目光一直带到塔顶,但是那嶙峋的斜坡太陡了,无可托趾,而仰瞥的角度也太高了,怎堪久留,所以冒险攀援的目光立刻又失足滑落,直跌下来。
这圣维往斯大教堂起建于一三四四年,朝西这边的新哥德式双塔却是十九世纪末所筑,高八十二公尺,门顶的人瓣玫瑰大窗直径为十公尺点四,彩色玻璃绘的是创世纪。凡此都是后来才得知的,当时大家辛苦攀望,昏昏的夜空中只见这双塔肃立争高,被脚灯从下照明,宛若梦游所见,当然不遑辨认玫瑰窗的主题。
菌西领着我们,在布拉格堡深宫巨寺交错重叠的光影之间一路向东,摸索出路。她兼擅德文与俄文,两者均为布拉格的征服者所使用,所以她领着我们问路、点菜,都用德文。其实捷克语文出于斯拉夫系,为其西支,与俄文接近。以“茶”一字为例,欧洲各国皆用中文的发音,捷克文说caj,和俄文chay一样,是学国语。德文说Tee,却和英文一样了,是学闽南语。
在暖黄的街灯指引下,我们沿着灰紫色砖砌的坡道,一路走向这城堡的后门。布拉格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,但显然都不在堡里。寒寂无风的空气中,只有六人的笑语和足音,在迤逦的荒巷里隐隐回荡。巷长而斜,整洁而又干净,偶尔有车驶过,轮胎在砖道上磨出细密而急聚的声响,恍若阵雨由远而近,复归于远,听来很有情韵。
终于我们走出了城堡,回顾堡门,两侧各有一名卫兵站岗。想起卡夫卡的K欲进入一神秘的古堡而不得其门,我们从一座深堡中却得其门而出,也许是象征布拉格的自由了,现在是开明的总统,也是杰出的戏剧家,哈维尔(Vaclav Havel,1936—),坐在这布拉格堡里办公。
堡门右侧,地势突出成悬崖,上有看台,还围着二段残留的古堞。凭堞远眺,越过万户起伏的屋顶和静静北流的魔涛河,东岸的灯火尽在眼底。夜色迷离,第一次俯瞰这陌生的名城,自然难有指认的惊喜,但满城金黄的灯火,丛丛簇簇,宛若光蕊,那一盘温柔而神秘的金辉,令人目暖而神驰,尽管陌生,却感其似曾相识,直疑是梦境。也难怪布拉格叫做黄金城。
而在这一片高低迤逦远近交错的灯网之中,有一排金黄色分外显赫,互相呼应着凌水而波,正在我们东南。那应该是——啊,有名的查理大桥了。首西欣然点头,笑说正是。
于是我们振奋精神,重举倦足,在土黄的宫墙外,沿着织成图案的古老石阶,步下山去。
而现在,我们竟然立在桥心,回顾刚才摸索而出的古寺深宫,忽已矗现在彼岸,变成了幻异蛊人的空中楼阁、梦中城堡。真的,我们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吗?这庄周式的疑问,即使问桥下北逝的流水,这千年古都的见证人,除了不置可否的潺潺之外,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。
2查理大桥
过了两天,我们又去那座着魔的查理大桥(Charles Bridge,捷克文为Karluv most)。魔涛河(Moldau,捷克文为Vltava)上架桥十二,只有这条查理大桥不能通车,只可徒步,难怪行人都喜欢由此过桥。说是过桥,其实是游桥。因为桥上不但可以俯观流水,还可以远眺两岸:凝望流水久了,会有点受它催眠,也就是出神吧;而从桥上看岸,不但左右逢源,而且因为够远,正是美感的距离。如果桥上不起车尘,更可从容漫步。如果桥上有人卖艺,或有雕刻可观,当然就更动人。这些条件查理大桥无不具备,所以行人多在桥上流连,并不急于过桥:手段,反而胜于目的。
4犹太区
石,砂岩的墓碑年代古远,大理石碑当较晚期。
“这一大片迷魂石阵,”转过头去我对天恩说,“可称为布拉格的碑林。”
“一点也不错,”天恩走近来,“可是怎么只有石碑,不见坟墓?”
茵西也走过来,一面翻阅小册子,说道:“据说是石上填土,土上再立碑,共有十层之深。”
“真是不可思议,”隐地也拎着相机,追了上来。四顾不见邦绶,我存和我问首西,茵西笑答:
“她在外面等我们呢。她说,黄昏的时候莫看坟墓。”
经此一说,大家都有点惴惴不安了,更觉得墓地的阴森加重了秋深的萧瑟。一时众人截然面对群碑,天色似乎也暗了一层。
“扰攘一生,也不过留下一块顽石。”天恩感叹。
“能留下一块碑就不错了,”茵西说。“二次大战期间,纳粹在这一带杀害了七万多犹太人。这些冤魂在犹太教堂的纪念墙上,每个人的名字和年份只占了短短窄窄一小行而已——”
“真的啊?”隐地说。“在哪里呢?”
“就在隔壁的教堂,”茵西说。“跟我来吧。”
墓地入口处有一座巴洛克式的小教堂,叫做克劳兹教堂(Klaus Synagogue),里面展出古希伯莱文的手稿和名贵的版书,但令人低徊难遣的,却是楼上收集的儿童作品。那一幅幅天真烂漫的素描和水彩,线条活泼,构图单纯,色调生动,在稚拙之中流露出童真的淘气、谐趣。观其潜力,若是加以培养,未必不能成就来日的米罗或克利。但是,看过了旁边的说明之后,你忽然笑不起来了。原来这些孩子都是纳粹占领期间关在泰瑞辛(Terezin)集中营里的小俘虏。当别的孩子在唱儿歌看童话,他们却挤在窒息的货车厢里,被押去令人哈咳而绝的毒气室,那灭族的屠场。
脚步沉重,心情更低沉,我们又去南边的一座教堂。那是十五世纪所建的文艺复兴式古屋,叫平卡斯教堂(Pinkas Synagogue),正在翻修。进得内堂,迎面是一股悲肃空廓的气氛,已经直觉事态严重。窗高而小,下面只有一面又一面石壁,令人绝望地仰面窥天,呼吸不畅,如在地牢。高峻峭起的石壁,一幅连接着一幅,从高出人头的上端,密密麻麻,几乎是不留余地,令人的目光难以举步,一排排横刻着死者的姓名和遇难的日期,名字用血的红色,死期用讣闻的黑色,一直排列到墙角。我们看得眼花而鼻酸。凑近去细审徐读,才把这灭族的浩劫一一还原成家庭的噩耗。我站在刀部的墙下,发现竟有心理学家佛洛依德的宗亲,是这样刻的:
FREUD Artur 17. V 1887—1.X 1944 Flora 24.Ⅱ 1893——1. X 1944
这么一排字,一个悲痛的极短裙,就说尽了这对苦命夫妻的一生。丈夫阿瑟·佛洛依德比妻子芙罗拉大六岁,两人同日遇难,均死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一日,丈夫五十七岁,妻子五十一岁,其时离大战结束不过七个月,竟也难逃劫数。另有一家人与汉学家佛朗科同姓,刻列如下:
FRANKL leo 28.11904——26.X 1942 Olga 16.Ⅲ1910—26. X 1942 Pavel 2. W 1938—26.X 1942
足见一家三口也是同日遭劫,死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,爸爸利欧只有三十八岁,妈妈娥佳只有三十二岁,男孩巴维才四岁呢。仅此一幅就摩肩接踵,横列了近二百排之多,几乎任挑一家来核对,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死去,偶有例外,也差得不多。在接近墙脚的地方,我发现佛来歇一家三代的死期:
FLEISCHER Adolf 15.X 1872——6.Ⅵ 1943 Hermina20.Ⅶ 1874—18.Ⅶ1943 Oscar 29.Ⅳ 1902—28.Ⅳ1942 Gerda 12.Ⅳ 1913-28.Ⅳ 1942 Jiri 23.X 1937-28.Ⅳ 1942
根据这一串不祥数字,当可推测祖父阿道夫死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,享年(恩年?)七十一岁,祖母海敏娜比他晚死约一个半月,恩年六十九岁:那一个半月她的悲恸或忧疑可想而知。至于父亲奥斯卡,母亲葛儿妲,孩子吉瑞,则早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同时殒命,但祖父母是否知道,仅凭这一行半行数字却难推想。
我一路看过去,心乱而眼酸,一面面石壁向我压来,令我窒息。七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具赤裸裸的尸体,从耄耋到稚婴,在绝望而封闭的毒气室巨墓里扭曲着挣扎着死去,千肢万骸向我一铲铲一车车抛来投来,将我一层层一叠叠压盖在下面。于是七万个名字,七万不甘冤死的鬼魂,在这一面面密麻麻的哭墙上一起恸哭了起来,灭族的哭声、喊声,夫喊妻,母叫子,祖呼孙,那样高分贝的悲痛和怨恨,向我衰弱的耳神经汹涌而来,历史的余波回响卷成灭顶的大漩涡,将我卷进……我听见在战争的深处母亲喊我的回声。
南京大屠杀,重庆大轰炸,我的哭墙在何处?眼前这石壁上,无论多么拥挤,七万多犹太冤魂总算已各就各位,丈夫靠着亡妻,夭儿偎着生母,还有可供凭吊的方寸归宿。但我的同胞族人,武士刀夷烧弹下那许多孤魂野鬼,无名无姓,无宗无亲,无碑无坟,天地间,何曾有一面半面的哭墙供人指认?
5卡夫卡
今日留居在布拉格的犹太人,已经不多了。曾经,他们有功于发展黄金城的经济与文化,但是往往赢不到当地捷克人的友谊。最狠的还是希特勒。他的计划是要“彻底解决”,只保留一座“灭族绝种博物馆”,那就是今日幸存的六座犹太教堂和一座犹太公墓。
德文与捷克文并为捷克的文学语言。里尔克(R.M.Rilke,1875——1926)、费尔非(Franz Werfel,1890—1945)、卡夫卡(Franz Kafka,1883—1924)同为诞生于布拉格的德语作家,但是前二人的交游不出犹太与德裔的圈子,倒是犹太裔的卡夫卡有意和当地的捷克人来往,并且公开支持社会主义。
然而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,卡夫卡始终突不破自己的困境,注定要不快乐一生。身为犹太种,他成为反犹太的对象。来自德语家庭,他得承受捷克人民的敌视。父亲是殷商,他又不见容于无产阶级。另一层不快则由于厌恨自己的职业:他在“劳工意外保险协会”一连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,也难怪他对官僚制度的荒谬着墨尤多。
此外,卡夫卡和女人之间亦多矛盾:他先后订过两次婚,都没有下文。但是一直压迫着他、使他的人格扭曲变形的,是他那壮硕而独断的父亲。在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里,卡夫卡怪父亲不了解他,使他丧失信心,并且产生罪恶感。他父亲甚至骂他做“虫豸”(ein ungeziefer)。紧张的家庭生活,强烈的宗教疑问,不断折磨着他。在《审判》、《城堡》、《变形记》等作品中,年轻的主角总是遭受父权人物或当局误解、误判、虐待,甚至杀害。
就这么,这苦闷而焦虑的心灵在昼魇里徘徊梦游,一生都自困于布拉格的迷宫,直到末年,才因肺病死于维也纳近郊的疗养院。生前他发表的作品太少,未能成名,甚至临终都嘱友人布洛德(Max Brod)将他的遗稿一烧了之。幸而布洛德不但不听他的,反而将那些杰作,连同三千页的日记、书信,都编妥印出。不幸在纳粹然后是共产党的政权下,这些作品都无法流通。一九三一年,他的许多手稿被盖世太保没收,从此没有下文。后来,他的三个姊妹都被送去集中营,惨遭杀害。
直到五十年代,在卡夫卡死后三十年,他的德文作品才译成了捷克文,并经苏格兰诗人缪尔夫妇(Edwin and Willa Muir)译成英文。
布拉格,美丽而悲哀的黄金城,其犹太经验尤其可哀。这金碧辉煌的文化古都,到处都听得见卡夫卡咳嗽的回声。最富于市井风味历史趣味的老城广场(Staromestske namesti),有一座十八世纪洛可可式的金斯基宫,卡夫卡就在里面的德文学校读过书,他的父亲也在里面开过时装配件店。广场的对面,还有卡夫卡艺廊。犹太区的入口处,梅索街五号有卡夫卡的雕像。许多书店的橱窗里都摆着他的书,挂着他的画像。
画中的卡夫卡浓眉大眼,忧郁的眼神满含焦灼,那一对瞳仁正是高高的狱窗,深囚的灵魂就攀在窗口向外窥探。黑发蓄成平头、低压在额头上。招风的大耳朵突出于两侧,警醒得似乎在收听什么可疑、可惊的动静。挺直的鼻梁,轮廓刚劲地从眉心削落下来,被丰满而富感性的嘴唇托个正着。
布拉格的迷宫把彷徨的卡夫卡困成了一场恶梦,最后这恶梦却回过头来,为这座黄金城加上了桂冠。
于是我们随智者过桥,再过六百年的查理大桥。白鸥飞起,回头是岸。
一九九五年一月